从《百喻经》看“得”字的发展
摘要
关键词
语法化 语义
正文
以下列出《百喻经》中的“得”字,根据字在句子中语义的虚实大致分为两组,尽管这样划分是不精确的,我们下文具体论述。
我们大致可以看出,《百喻经》中的“得”,作为实意动词“获得”的要远远多于虚化后的用法。现在我们来简要分析“得”字的各种用法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可以看出,“得”字最典型或者最原型的用法是出现在体词或体词短语前的,表示“获得”,强调的是结果,并不强调通过何种手段,正是由于“得”本义的宽泛性,才使得它能够出现在多种语境中。试比较:
1、既得盐美,便自念言:“所以美者,缘有盐故。少有尚尔,况复多也?”《愚人食盐喻》
2、譬彼外道,闻节饮食可以得道,即便断食。 《愚人食盐喻》
两个句子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,但是,“盐”是具体名词,而“道”是抽象名词,也就是从认知上来说,人们对“得”的用法已经由具体到抽象了。而人们对复杂事件的整体认知也能从如下句子中感受到:
11、往有商人,贷他半钱,久不得偿,即便往债。 《债半钱喻》
我们说典型名词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,典型动词则是基本图式的复合。“偿”可以作为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事件来理解的,“获得”的对象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事件,这离“得”的原型用法似乎相去就更远了点。以上都体现了语言的包容度,正由于此,语言才能不断地发展。在语篇中,由于上下文文义的补充,我们可以适当地运用省略形式,因此,典型的结构“得+宾”中的宾语被省略掉了,但是,我们发现,这样的句子中的“得”往往不是以光杆形式出现的,如下所示:
14、后欲求佛果,终不可得。如彼焦种,无复生理。 《种熬胡麻子喻》
24、此树高广,虽欲食之,何由能得。 《斫树取果喻》
13、以其难得,便生退心:不如发心,求声闻果,速断生死,作阿罗汉。 《入海取沉水喻》
30、二鬼愕然,竟无所得。 《毗舍阇鬼喻》35、若得遇佛众人疲厌,都无所得。 《构驴乳喻》
52、众人疲厌,都无所得。 《构驴乳喻》
尽管我们发现这例子中有的“得”已经处在“所字结构中”,整个所字结构用做前面动词的宾语,但是不难看出,句子里要么会有助动词“能”“可”等表达一种情态,要么前面也会有“竟”“都”等表达范围或者时间,总之,句子传递出的信息是,一件事的最终结局不如人意,所以这样的“得”也就经常出现在否定句中。而原文信息中给过的宾语却被省略掉了,也就是意味着宾语所代表的具体信息不再重要,“结果”成为了最终表达的重心,这就体现在了“得”的身上。这样了语义凸显的转移与变化,似乎与其本义“获得”有点距离,但是从认知角度考虑,却也很好理解。“获得”是经过努力而有所收获,但当人们的语义凸显只聚焦到整个事件的最后的点上时候,也就是“结果”,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转喻。
我们发现,“得”后加体词性短语的时候都是作为动词“获得”义的,但是它后面出现兼类词的时候就很难断定“得”到底应该充当什么角色了,例如:
28、汝欲得离者,当摄汝六情,闭其心意,妄想不生,便得解脱。 《饮木筒水喻》
51、“生死之中,无常苦空无我,离断、 常二边,处于中道,于此中过,可得解脱。”
《摩尼水窦喻》
“解脱”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(如果在当时“解脱”已经通过转化成为兼类词),那么这两个句子中,如果“解脱”作动词,那么“得”就都可以省略而不影响句义,得到“便解脱、可解脱”,这时候“得”就成为一个表情态的助动词。如果“解脱”为名词,那么“得”依然是一个实意动词,做句子的谓语。但是“得”的本义不可能一下子虚化到助动词。所以由实词到助动词的发展脉络就是我们要探寻的。上文推论过“得”由“获得”义通过语义凸显侧面【2】的转变而仅表示“结果”,那么结果也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已经实现的,一种是说话时候没实现而预期未来将要实现的,也就是“结果”可以分为已然和未然,已然的就理所当然地表示结果,而未然就成了一种“可能”。我们再来看上面两个句子,联系句义,我们也发现,这两个句子所表达的并非已经实现的,大致的意思都是“如果做到什么什么,就可能怎样怎样”,句子中的“便、可”也是表达这种可能性的。这样的句子里,“得”作实意动词理解会更自然一些,这时候前面的“可、便”就是修饰语,但是不难看出,此时的“得”已经具有了“可能”的意味。
我们再来分析“得+谓词”这类结构,其中的谓词同样包含动词和形容词性词组,如下例:
1、甘蔗极甜,若压取汁,还灌甘蔗树,甘美必甚,得胜于彼。 《灌甘蔗喻》
12、食六枚半已,便得饱满。 《欲食半饼喻》
15、已得出家,得近师长,以小呵责,即便逃走。 《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》
20、而此病者,市得一雉,食之已尽,更不复食。 获得意或者结果意《病人食雉肉喻》
后跟谓词性短语的“得”,与其说它的“获得”义还在,不如说它的“结果”义更明显了(由于“可能”义来自于“结果”义,表示未然的结果,所以用“结果”来总体表示“结果和可能”)。比如例1中的“得胜于彼”与上一句的“甘必美甚”的“必”相对应,都表示可能;例12中的“便得饱满”表示的是吃了六个半结束后就饱了,表示结果;例15中的“已得出家”,“已”就是表完成,“得”加强了其“结果”义;例20中的“得”,如果理解为“获得”义就不很恰当了,因为后文中“食之已尽”表示“雉”已经被吃完了,那么买雉的食就应该是过去完成体的,而“得”在这里表示“完成”义更合理,这里有些类似于现代汉语的“了”表示完成体。以上其他结构中,“得”从功能上来说,应该定义为助动词。
从“得”所处在的环境来看,“得+体词”是原型结构,也是“获得”义的典型结构,“得”如果跟谓词性短语结合,“得+谓词”,得的意义就会变虚,从认知角度来说就是将语义凸显的点切换到了“结果”。当然任何划分都没发做到一刀切的,因为词义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。有时候,“得+V”也是作为连动结构出现的:
44、时妇为夫造设饮食,夫得急吞,不避其热。 《效其祖先急速食喻》
这里的“得”表示“得到食物”之后狼吞虎咽,是一个连动结构。由此,我们认为,“得”的虚化不仅与其所出现的位置有关,也与句子的语义环境有关。只有当结构中的有比“得”的动词义更强的谓词的时候,“得”才有可能退作背景信息而虚化。总 ,“ 得 ” 在语义上的抽象性是它语义语法变化的基础, 这使得它在动词前后都会地位下降。【2】
我们看到,《百喻经》中还没有“V+得+C”的述补结构,用的都是“V+受事+C”,例如:以梨打头破。这能从反面证明,当时的“得”还没有虚化到可以作补语标记的程度,虽然作为助动词可以表“结果、可能、完成”,但是依然没有典型的“V+得+C”出现。而我们通过以上分析,可以大致推理出,现代汉语的组合式述补结构“V+得+C”来自助动词“得”。现代汉语中,该结构的解释也有两种,例如,以“写得好”为例,可以理解为1、表示结果,对已经写完的对象的评价。2、还没有写,是对能力的猜测,表示可能。这两个例子从表以来看也与助动词相符,因此,我们推理现代汉语中的作为补语标记的“得”来自助动词“得”。
在现代汉语中,“得”有时候也以语素的形式出现在词中,例如:得道、迫不得已、得逞等等,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词汇化的结果,他们在汉语史上都曾作为词组出现,而出现的频率多是词汇化的助推剂,在这些已经凝固的词中,我们仍能看到词的本义。
到此,我们可以给“得”的发展做出一个简单的脉络图:
动词,获得→助动词,结果/可能(体标记指初现端倪表示完成)→动补结构中补语标记
“汉语的虚词大多来自于实词,也就是说是实词虚化而来的,实词虚化是以意义为依据,以句法地位的固定为途径的,属于词汇*语法范畴。汉语中许多新语法手段,新句式的产生,大多是与实词的虚化相伴随着实现的。”【3】这段话很深刻地阐释了汉语词的演变脉络,也是我们本文“得”字演变的一个总结。解惠全老师将词的虚化比作母羊下羔羊,一个实词虚化之后其实词意义一般都还存在,而虚化的词有的能存活,有的半路夭折,最后的面貌就是一词多义,但是意义之间是有联系的,只不过这种联系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。
参考文献:
【1】认知语法基础;兰盖克
【2】《百喻经》 “ 得 ”字用例浅说,尤慎,零陵师专学报1994。
【3】古书虚词通释,解惠全
【4】近代汉语语法;吴福祥
【5】认知语言学;王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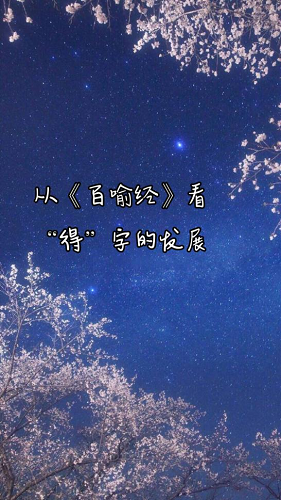
...